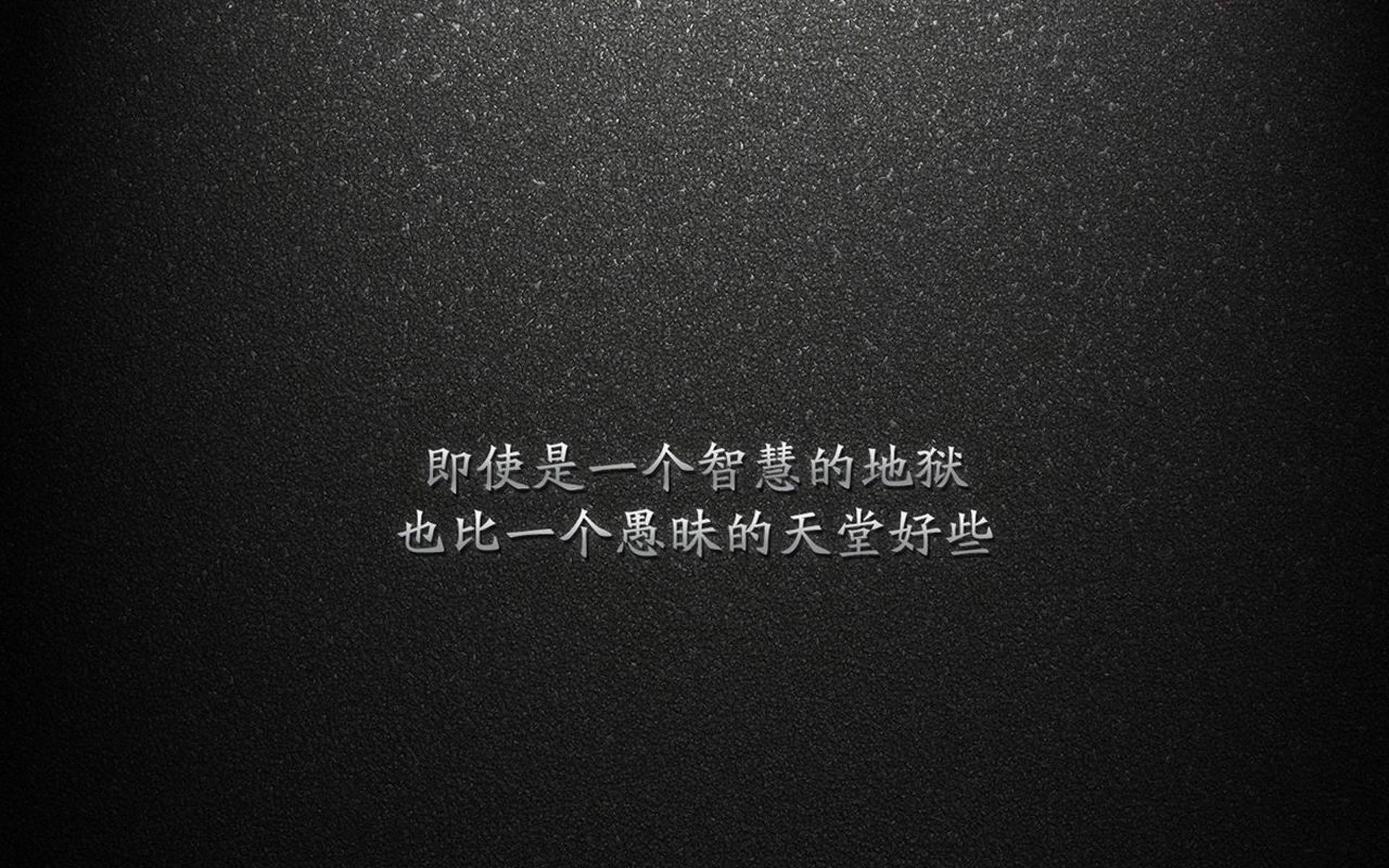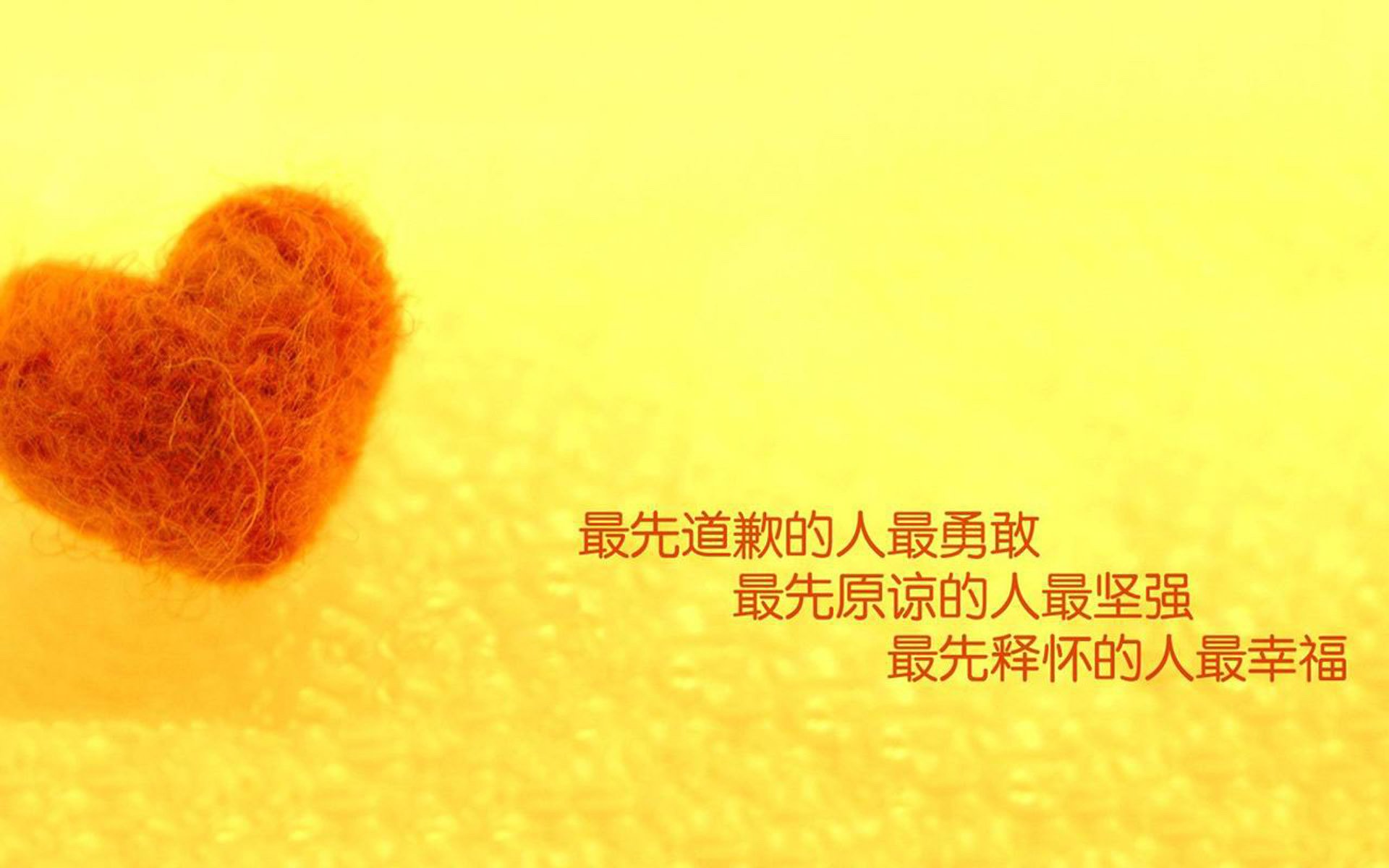啊扶着她的腰直挺(感觉腰挺不直)
啊,把她的腰撑直了(感觉不直)
一个
白的心情很好。
他从上海来到北平,是因为听说玻璃厂有人在卖一幅唐寅的《秋风万扇》。他收藏的字画很多,空白色是明朝才出现的。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,它似乎总是不完整的。
卖家要价极高,竞争对手众多。嘉柏是最会说话的一个,不仅不讲价,还承诺以两倍的价格购买。很难找到这么好的客户,交易很快就完成了。
他兴致勃勃的去了地摊,捡了些漏,都是真品宝贝,让跟着他的人拿回去。
前面有一群吵闹的人,围着一个小摊子。白佳走过去看看是什么。原来是个卖画的女生。她把画举得高高的,喊道:“每个人都可以好看。世界上只有一幅这位著名艺术家的画。路过不要错过。”
水汪汪的大眼睛,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身前,穿着蓝色的上衣和粗布裤子。这是苏维扬留给嘉柏的第一印象。
有人喊:“我出五十块钱。”
一开始有人跟着说:“我给你八十。”
“一百块卖给我。”
“一百五。”
……
价格每高一点,苏维扬脸上的笑容就加深一分,300就要成交了。佳白很好奇,看了一眼这幅画。

水墨晕染的写意,素衣女子回眸一笑,眉远似戴,目明如身后的碧水,人与景交融得恰到好处,在山川右侧留下了一片空白。贾立刻就看中了它。他挥动袖子。“我给你500。”
顿时,人群鸦雀无声,就这样一锤定音,嘉柏拿下了这幅画。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,苏维扬在交易过程中警惕地看着他,眼睛睁得大大的,好像怕他违约。白政正要拿出钱给她,突然有了调侃的心思。
“对不起,姑娘,我刚才不耐烦了。我真的只有两百。”
“你……”未央以为自己猜对了,没好气地说:“一个穷小子,学什么大家族附庸风雅!”
她很不耐烦,像一只发疯的小猫一样张牙舞爪,但她不可能有恶意。
他差点笑出声来。
“这幅画是什么样的优雅?在我看来,它连一毛钱都不值。”佳柏作势看着这幅画,然后又矫情地盯着苏维扬。“还是个皮肤外表很好的姑娘。它值几美元。能卖吗?”
他的语气轻浮,像个纨绔子弟。未央先是被他羞辱的画,接着又被他轻佻的言语调戏,忍不住怒道,“我不是窑姐,”她跑过去把画抢回来,“还给我!我不会卖的。”
贾把她的胳膊往后一拉,那幅画就轻而易举地落进了她的怀里。似乎苏维扬这个局外人似乎对他投怀送抱。他恶狠狠地看着她,摇摇头,“没关系。我吃点亏不要紧,但我不能再叫别人来忽悠你了。”
仿佛站在了右边,丢下200大洋,扬长而去。未央恨得咬牙切齿,冲着他的背影喊道:“别让我再看到你。”
对方似乎笑得更厉害了,还能听出他慵懒的声音。“姑娘若想讨债,我慕容家白,随时恭候。”
2
贾的父亲穆玉清是上海的一个黑帮势力。他膝下有两个儿子。长子贾平是他第一任妻子所生。白佳是他的私生子。他爱那个女人,但她拒绝嫁给他。生下白佳后,她很快就因体弱多病而去世。
贾长得像他妈,一双桃花眼,鼻子挺得笔直,看似翘却不翘的桃花眼,总让人觉得诱人的薄嘴唇。他天生帅气,也是慕雨晴的最爱。
“你得到什么了吗?”穆昱青拿着一个小玉瓷杯,问他:
“嗯。”贾霸玩的是一把中唐的薛瑞万扇,音色很随意。
“你什么时候帮你弟弟打理赌场?”
“没必要,”他站了起来。“我做不到。”
穆家平打理着穆公馆在上海的大部分产业。穆青更喜欢嘉柏,想让他接手自己的事业,但正是因为他的喜欢,他更不愿意强迫他。
穆的幼子在上海租界以潇洒随性著称。有人把他比作王羲之,他文笔好,对打仗无动于衷。而且他在文物鉴赏方面的眼力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。
白非常喜欢古董,凡是她喜欢的东西,她都要设法拿回来。
他端详着桌上摊开的水墨画,想起了那个语气强硬的女孩,眼里捕捉到一丝笑意。
那已经是苏维扬来上海一个月之后了。
在乔佛尔大街有一家理发店,是嘉柏一直打理的。他一个月没刮胡子了,胡子长满了下巴。
苏维扬剪头发的时候没认出来,小心翼翼的左顾右盼。
白憋住笑,低声问,“你是新来的吧?技术太生疏了。”
她点头道歉。“非常抱歉,先生。我去叫师傅。”
“不,”佳柏假装生气。“把我的胡子剃了就行了。”
顾客是上帝。虽然苏维扬心里已经把这个难缠的客人骂了千百遍,但表面上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弯下腰,一点一点地把胡子剃掉。
一张干净帅气的脸出现在她面前。当她震惊的时候,手里的力量稍微增加了一些。贾百奇先是闭上眼睛,乐在其中。这时,她痛得大叫起来,“你是猪吗?让你剃光头而不是杀人!”
苏维扬幸灾乐祸地看着下巴上的红印子,皮笑肉不笑。“这不是慕容嘉柏吗?好久不见。”
贾真诚地笑了。“你能记得我,是我的荣幸。”
她迅速把剃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“废话少说,把欠的钱还了。”
白佳一点也不惊慌。他笑了笑,然后用更快的速度和力度把剃刀抓到自己手里,用左手握住苏维扬的双手。
未央反应过来,拼命想挣脱,那人力气太大,她手腕越动,越疼。
贾的眉头在手掌碰到自己手掌的那一瞬间轻轻皱起。“别动,”他站起来,转身把她按在座位上。他的右手在未央没有察觉的情况下,用剪刀代替了剃刀。
随着白色的剪刀在纤细干净的手中飞舞,穆家白在未央的目瞪口呆中剪掉了她织成辫子的两根头发,齐腰的头发立刻变成了带耳朵的短发。白人用木梳轻轻梳理,“咔嚓咔嚓”几下剪在一起,镜子里的女人清晰利落,更加灵动。
显然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,贾白树皱起了眉头。“顺眼多了。”
眼前的女人就像一个讨喜的瓷娃娃,她的眉眼,她的口鼻,开心时的笑容,甚至失意时微微隆起的下巴帮,都是他喜欢的特征。
他打领带时,吻了她的嘴角。
苏维扬愣住了,忘记了这个男人跟自己有什么样的仇。此时的她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小女孩,脸红了。
心中还在生气,他怎么会这么轻浮。
“我慕容嘉柏很少剪人的头发。人们说我值一千美元。除了欠你的三百大洋,其余的我都不要。”那人镇定自若,像个恋爱老手,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。“这么说,你赚了。”
看来刚才那个吻只是我睡梦中的一个意外。
白说着拿起椅背上的黑色长风衣。“苏小姐,”他看了一眼她灰蓝色短上衣上的工作证。“苏未央”二字清秀工整。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
修长苗条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长街里,苏维扬摸了摸自己的唇角,感觉不知所措。
三
苏维扬换了衣服,拐进一条巷子,从后门进了祁家的花园楼。
她无声无息地进进出出,轻如鸿毛,训练有素。所以当她出现在陆弃面前时,他毫无察觉。
贾的技术和审美都很优秀。就连一向对女性吹毛求疵的陆弃,在看到未央的新发型时也大吃一惊。齐肩的长发轻柔的垂在两侧,让她的皮肤更加白皙,五官更加精致。
“叔叔。”眼睛没有垂下来。
陆淡淡一笑,一副君子模样。他说:“未央现在真的长大了。”语气中有调侃之意。
未央是祁家的养女。
十年前的上海,真的只有一个苏家。不管是商界还是政界,白道还是黑道,永远是苏家往东,别人不敢往西。但是,时局动荡,繁华终有尽头。
繁华的苏家大院一夜之间化为灰烬,只剩下当时年仅八岁的未央。要不是世交齐出手相救,恐怕这个珍贵的姓氏早就没了。
徘徊了很久,思绪被强行拉回。未央竭力装出平静的样子,问道:“叔叔叫我回来有什么事?”
怀仁点点头。“明晚,穆玉清的50岁生日,是做这件事的最佳时机。”
苏未央眉眼无波,微微颔首,回房准备。女仆已经送来了最新款式的连衣裙、玉镯、玛瑙耳环和翡翠项链,装满了整个抽屉。
她无疑是整个会场最光鲜亮丽的一个。十七八岁是一个女孩子最美好的时光。她身上有一种风尘的气质,让上海这个大染缸里的男人们既向往又恐惧。
明亮的眼睛向他抛媚眼,使得张省长的心尖颤着大肚子。然后他绕过人群,双手很自然的揽着苏维扬的纤腰。
在角落里拼命喝酒的穆家白,无聊地扫过豪宅里珠光宝气的人群,但当她瞥见一个有钱人怀里天真少女熟悉的身影时,瞳孔突然收缩了。
未央低头不知道说什么,张省长面带微笑,脸上的肥肉都堆在一起了。
由于胸中有一团怒火,佳白变得越来越狂躁。手上一用力,小小的郁金香形红酒杯就这么被硬生生地打碎了。
不知道是哪个一直坐在他身边伺机而动的女儿吓得尖叫起来。嘉柏不耐烦地望了一眼,小姐脸色瞬间变得苍白,不敢再出声。

舞池里音乐刚刚响起,张省长正准备带着一朵漂亮的花尽快起舞,却见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径直朝他走来。
从未涉足商人和政治的穆家白,被张省长听说有一段时间了。他曾经花了很多钱买他的一幅字画,却被无情地拒绝了。
白向张省长微微倾身,低声道:“敢问张省长,我可不可以请你旁边的这位小姐跳支舞?”
未央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,慵懒中带着一点威胁,这不就是那个自称慕容嘉柏的男人吗?
他的到来让她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心。
再舍不得怀里温香软玉,也要卖木玉清一个面子。省长张对未央眨了眨眼睛。“能和你跳舞是她的福气。”
在紧握双手的一瞬间,两个人都漏了一拍。慕白握住一只柔软的小手,能感觉到主人的颤抖。
未央手心冒汗。
贾暗笑,看着那近在眼前的女子脸上淡淡的红晕,羞得不敢抬头看他。刚才她心情的轻松一扫而光空。
“为什么?怕我?”他温暖的呼吸萦绕在她身上,创造了一个暧昧空的房间。
“谁说的!”未央愤怒地抬起头,却发现自己被困在那双充满笑意的桃花眼里,心里暗暗恼火。
“你怎么来了?”未央想起什么,问道。
“如果允许你来,我就不准去凑热闹了?”白和她一起堵嘴,乐此不疲。
“我是说,你到底是谁?”她很困惑。
他们两个跟着唱片里荡漾出来的欢快的曲调,舞池里还有其他许多男男女女,但没有其他一对像他们一样合拍而美丽的情侣。
“我不是告诉过你,我是江湖浪子,慕容家白——买你画剪你头发的穷小子。”
提起之前的事情,苏维扬又气又恼。她低头看了看那两个人的脚步声,轻轻的“咔”了一声。
不,她会相信的。
然而,她的下巴在被抬起的时候猝不及防。那个男人一只手搂着她的腰,另一只手抬起来,她带关节的食指挑着她的下巴,强迫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。
他的笑容真的很美,世界上最美的音乐也没有他说的那么美。苏维扬觉得自己应该堕落了。
白木凝视着苏维扬,他的眼睛充满了他自己从未注意到的深情。他说:“不要低头。你今晚真美。我想多看看你。”
四
张省长深有感触。当穆家柏向他鞠躬时,他真的吓了一跳。白木冷酷而高傲,没有人看不起他,更不用说礼仪了,他从来不不屑。
他远远地看着舞池里的两个人,突然觉得他们真的很像。哪怕是一个温暖的微笑,带着一点对尘世的疏离,也总能在喧嚣的人群中营造出一个安静的地方。
就在刚才,穆加白在进舞池前悄悄对他说:“明天早上八点,在花园别墅里,总督会看中白佳的一部拙劣的作品,他自己选就行了。”
穆小儿子字画千金难求。张省长认为这次他可以吹嘘一阵子了。
然而,他不知道自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
宴会结束时,张巡抚喝得酩酊大醉,苏维扬扶他到府邸自己的房间里休息。这是她第一次出任务,刺杀张巡抚,谈不上顺利,却被空给钻了。总督府一时内乱,巡抚张脱不了身。那时候他身边没有男生。这真是天赐良机。
未央很快找出了她早已藏起来的刀,刺入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心脏,一刀毙命。
她浑身发抖,衣服上溅满了血。她一边跑,一边想:“我逃不掉了。”
人群已经散去,室内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。未央对道路不是很熟悉,只觉得偌大的府邸如同迷宫,又回到了原点。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,未央惊魂未定,踉跄了几步,突然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
门“啪”的一声关上了,她刚想喊,却错过了看着那双关切的眼睛停下来。
贾一直保持着抱紧她的姿势,悄悄做了个“安静”的手势。
未央淹没在那双深邃的眼眸中,不知为何定下心神。她挣脱了他的怀抱,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:“我可恨吗?居然杀了人。”
白带着痛苦的表情看着她。“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。”在理发店的时候,他摸了摸她的右手,她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道厚厚的老茧,那是多年舞刀弄枪的痕迹。他温柔的安抚她,“是第一次杀人吗?”
听到这里,未央的怨气慢慢升起,刺激着泪腺,眼泪像断了线一样流了下来。都说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。陆弃收养苏维扬并不完全是出于好心。暗杀是有预谋的,所以她必须接受命令并承担风险。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扶植的祁氏家族俱乐部,此时成为generate的赞助商。
“我真的不想……”断断续续地没有结束,但平日里最多是对着蚂蚱练。说到底,我还是个小女孩,杀她终究是残忍的。
贾像植物一样叹了口气。未央今晚的预谋,他猜对了,所以他放了她。她看起来很冷静,但她没有经验。如果我知道,他不会让她冒这个险。
“苏未央,”佳白轻声唤她。她眼里含着泪水,看不到他的表情。
“你将来想杀谁?我来帮你做。”
五
未央这一夜的睡眠是难得的安稳,昨晚人们说了什么,她实在记不清了。隐约听到门口有动静。一觉醒来,她看到了眉眼间带着笑意的穆家白。
他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表情,下一秒似乎在戏弄她。
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门被敲响了,外面传来一阵哗啦声:“这里是穆老师的休息室,不要查了。”
“嘿,过来。”
新上任的上海巡抚在穆公馆遇刺身亡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上海,各大报纸的头条都是血淋淋的场面。坐在茶馆里,悠闲地看着报纸,陆弃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苏真的女儿没有让他失望。
苏维扬躺在床上,却如坐针毡。
“怎么,我穆家白的人,就是你能怀疑的人?”白人声音冰冷,一脸不悦的朝着在房间里巡逻的一行人发出了逐客令。
“这个…”负责人眼尖,瞥了苏维扬一眼。”有人说看见苏小姐和张总督一起进出.”他的声音像苍蝇一样轻柔,从心底里有些害怕穆家白。
“请不要做不必要的调查,先生。苏小姐从昨晚起就没有离开过我。”他的语气中已经包含了一丝愤怒。“我们穆府的人,自然会把这件事向巡抚交代的。”
一行人终于走了,但未央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刚才那一行人对他的态度,以及一开始咄咄逼人的宣称,让她一下子就明白了,“你就是穆家的小公子,穆家白?”
如果是明显存疑,那显然是用不容置疑的语气。贾扬了扬好看的眉毛,声音也跟着变了。“没有?”
未央咬着嘴唇,摇摇头。她应该想到的。放眼整个上海,除了穆家白,还有哪个男人能这么迷人,身材匀称?
慕白的名字不仅在上海租界无人不知,而且家喻户晓。在北京的琉璃厂,文人提到他的名字,脸上也自有恭敬之色。来上海之前,她看到了嘉柏的字画,很是欣赏。作为一个才女,她知道自己配不上。
她还是觉得慕容适合他。人都渴望休息,他天生就有这样的风韵。
张死后不久,就有消息说穆先生和苏小姐交了朋友。报童拿着厚厚一叠报纸,很快被抢走空。黄包车上戴着纱手套的珠光宝气的富婆,茶馆里悠闲的白鬓老人,怀里抱着书走在多伦路上的女校学生,都在谈论这个,风头几乎盖过了不时传来的枪炮声。
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无论死亡有多艰难,人们对八卦的热情总是在燃烧。
现在是上海的十月,金秋时节。晚霞灿烂,安和寺路两旁的梧桐树被染成了金黄色。远远望去,道路蜿蜒如黄浦江,流光溢彩。
在英国帕拉蒂奥风格的花园洋房里,穿着黑色风衣的挺拔男子逆着光线站着,看上去和人一样冷漠,但眼睛却是明亮的。
“我怎么能告诉租界那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?”穆玉清抱着头,怒视着小儿子。
贾轻轻笑了笑。“有什么好解释的?”
“张是洋人任命的总督。他死在穆公馆。这不是说明我穆雨卿在打他们的脸吗?”
“说得好像你不愿意似的,我父亲应该感谢这位女士,这样你就不用亲自动手了。上海的省长职位不是你一直念念不忘的吗?”白木不玩,他一针见血。穆玉清早前投了很多钱进去,没有人比他更想要那个位置。
张肯定会死。
一席话让穆昱青出了一身冷汗,虽然他爱这个儿子,但心底也怕他。也不愧是自己的儿子。只提几件事,穆家白马上就能轻松掌握全局。
“也罢,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,但是你和那个女孩……”穆玉清痛苦地揉着太阳穴。他拿穆家柏毫无办法,但话音未落,眼前已经没有了人影。
未央是为了确定周围没有人才会溜进戚家。陆弃早已等在那里,他把手中的报纸递给了她。未央只一眼就看到了头条上穆家白的照片。哪怕这个人是随便坐的,也是那么好看。
匆匆看完,她脸红了,辩解道:“怎么了?我只见过穆先生一面,昨晚他还好心保护我。”
鲁不置可否,一切尽在掌握。现在张死了,穆一定会抓住机会,企图上位。表面平静之下,其实隐藏着惊涛骇浪。他必须尽快行动。
否则,十年前发生在苏真身上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在他身上。
十年前,他因为一时的心软,把一个孤女留在了苏家。他从来没有想到它在今天会有很大用处。十年前陆弃设计搞垮苏真,沉淀在时间长河中渐渐被埋没的真相,谁也没有想到,年仅十二岁的穆家白也知道一二。
六
为了不被外人抓住,苏维扬平日里还在理发店当学徒。各方面都隐藏的很好,有心人很难发现她和祁家有牵连。在上海女人眼里,她飞到了枝头,变成了凤凰。从未亲近过女人的穆家白,只对她青睐有加。
他对她真的很好。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他会骑着自行车带着她逛上海的大街小巷,在旧裁缝店里为她挑选最新款式的旗袍。即使在雨天,他也会撑着伞,给她带来他最喜欢的蝴蝶蛋糕。香味充满了这个小房间。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精致的水晶发夹,轻轻地别在她的头发上。
只是这个人一直说个不停,不是生她的气,就是逗她。
在忙空的时候,未央会看着剃须刀,微微陷入沉思。上次两人的消息见报后,她怕给他添麻烦,就约他出来解释。
谁知那人笑得脸色苍白,过了好一会儿才盯住她,道:“我穆家白从来不喜欢拿锅回去。反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,我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呢?”
未央这个人总是这样,对别人只是一本正经的语气,但他对她的心思是不安分的,随便说一句话就像逗她。
她之前住在齐家汇馆,接触的男人不多。但是这个人和她想的很不一样。他身材匀称,举止优雅,有一种正邪兼备的气质。他总觉得有馊主意,她却忍不住想靠近。
现在已经是初冬时节,一眼望去,繁华是萧条。这几年大的战争不多,上海是难得的和平,就像暴风雨前短暂的平静。
苏维扬一走出理发店,就撞上了一个结实的胸膛,有人在寒风中带来了一丝不该有的温暖。
木白头戴着一顶绅士帽,一件及膝的天鹅绒黑色外套,一双厚重的黑色沙漠靴让他更加帅气,一条长长的灰色丝巾为整个人增添了一丝柔和。
“怎么,我一天没见你,就觉得我得对你投怀送抱了?”
未央又舍不得跟他发脾气。
他拉着她的手,带她去了一个豪华的俱乐部会所,那里可能正在拍卖什么东西。一路上很多人跟他打招呼:“穆先生,上次看到一件永乐年间的青花瓷,有时间给我掌眼吗?”
未央看过嘉柏的藏品,爱之入骨。那些古老的东西都被历史洗过了,几百年了,一直平淡到现在。沉淀已久的美,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有人知道,有人愿意欣赏。这是一种无比的幸运。
贾把未央带到会场坐下。刚开始的时候,他一反常态的兴趣缺缺,就连他一直偏爱的玉雕也无法让他振作起来。当只轮到一幅看起来年轻的字画时,他坐直了身子,低声说:“来了!”
“这幅画是前上海市长苏真画的……”
苏维扬听到这个介绍,猛地抬头,吸了一口气,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贾听了,便问:“怎么了?”
“这是我父亲的画。你之前买的那本不是名家做的,但是我模仿了他的笔墨。这张确实是手写的。”她没有对嘉白隐瞒什么,实话实说。
白此时脸色微微变了变。他依稀记得十年前的一个月夜,他去苏真的公寓向他请教书法。结果他看到整个房子都被火淹没了。苏真歪坐在外交大楼的大门前,腹部中了两颗子弹。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
老老少少一直很合得来,讨论书法也总是很开心。那一天,他看到苏真死在自己面前,清楚地记得嘴里一直重复的三个字,“是陆弃。”
他在琉璃厂看到未央卖画的时候,不知怎么想起了那个和他父亲一样是老师的长辈,却没有想到是女儿的手。这次,他想买这幅水墨画来纪念他的老朋友。白木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,但他的眼睛总是向前看。他想到苏家的独生女已经死于那场大火,于是抑制住了复仇的欲望。
从前,他没有见过苏维扬几次。十年后,命运把她送给了他。
白木在她耳边低声说,“这是一个老朋友的女儿。我该叫你苏嘉人吗?”
为了保护自己,她改了名字。这时,有人叫她以前的名字,那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,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汽。
“你认识我?”未央哽咽着问道。
“自然,”佳白揉揉她的头发。“我只是没想到你还活着,而且这么漂亮。”
七
穆青最近头疼。法租界里不知有谁充耳不闻,早已断绝了与穆家的生意往来。但是最近一周左右,纺织厂亏损了几十万,搞得人心惶惶。
陆的公司越做越大,几乎盖过了穆的风头。两家人的头头明面上客气的握手,聊的很开心,暗地里早就闹翻了。然而齐鲁还没得意多久,就传来了穆小子要接替父亲的位置,打理租界上海赌场的消息。他还掌管穆手下的所有帮派。
我鄙视我大哥和我爸社交。他早就精通人情世故,是个人才。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完美的,让人挑不出毛病。
人们说起穆的幼子,已不再是当初单纯的赞叹,更多的是畏惧和崇敬。他在商业上非常足智多谋,天生一张独特的脸,笑容温和而无害。但是,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,他从不手软,是个“笑面虎”。
法国人提出再次与他们合作。
穆家平看出他野心勃勃,走火入魔。
“沐儿,凡事注意分寸。”他知道佳白已经动了真情。曾几何时,他只痴迷于收藏,看起来像个没文化的纨绔子弟。现在没有一次会议如此紧张。
“他们想要她死,所以我要整个上海市为她的生命买单。”白佳笑得邪灵,像《十八层地狱》里的阎罗王。
没办法,什么叫看到心爱的女人受任何委屈。那天,他问未央要不要报仇。小女孩的眼睛里满是鲜红的血,显然心中有着无限的仇恨。
他没有告诉她真相,所以他认为齐鲁暂时不会对她怎么样。敌人逍遥法外,逍遥法外,她却做噩梦,他不能视而不见。
未央也很担心自己的突然转变。她抿着嘴唇,轻轻地拉着他的裙子。“你……不用为我做这些。”
“哦?”白似乎并不领情。他转身走近她。“如果不是为了你,我这样做是为了谁?”
他面轻风轻,未央有些生气地收回了手,道:“我只是不想让你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”
他平时不喜勾心斗角,天性洒脱。因为她,他不得不去趟那浑水。
“孩子不是鱼,而是鱼的幸福?”白木漫不经心地对她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一种抚慰的意味。“我很乐意为你做任何事。”
他以为只要把祁家彻底推翻,就带她出上海,找个安全的地方放柴米油盐。但是,在这样的乱世,很多东西,一旦一头扎进去,就很难脱身,甚至冒着生命危险。
在齐的古典建筑前,院子里的女神喷泉在温暖的阳光下画出了彩色的图画。曾经争奇斗艳的花朵,走过了炎热的夏天,步入了萧瑟的秋日,已经凋零,失去了往日的色彩。